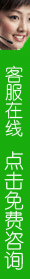案例:
2009年6月,某藥品監管部門在日常監督檢查中發現,B醫院使用的C廠家生產的批號為D的注射用輔酶A系用安瓿包裝,注射用輔酶A劑型為粉針劑。經調查,D批號的注射用輔酶A所用的包材安瓿是具有藥包材注冊證的合法藥品包裝材料,經核實,該注射用輔酶A申報資料顯示該藥品包裝材料為西林瓶。
分歧:
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于2002年6月2日發布了《淘汰落后生產能力、工藝和產品的目錄》(第三批),其中明確淘汰使用安瓿包裝粉針劑,具體執行時間為2002年7月1日。C廠家生產的批號為D的粉針劑注射用輔酶A在國家明令淘汰使用安瓿包裝粉針劑后依然使用安瓿包裝粉針劑,這一行為明顯不合法,但執法人員在該藥品定性和處理上產生了以下三種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可將該批藥品定性為劣藥。國家已明令淘汰使用安瓿包裝粉針劑,企業在申報藥品注冊時提供的申報材料也顯示該注射用輔酶A藥品包裝材料為西林瓶,企業在這種情況下依然使用了安瓿包裝注射用輔酶A,符合《藥品管理法》第四十九條第三款第(四)項“直接接觸藥品的包裝材料和容器未經批準的”情形,不能機械地認為藥品包裝材料產品本身未被批準獲得批準文號才符合這種情形。
第二種意見認為,應按《直接接觸藥品的包裝材料和容器管理辦法》進行處理。國家淘汰安瓿包裝粉針劑,是因為其不適合包裝粉針劑,所以對本案中的粉針劑而言,安瓿顯然屬不合格藥品包裝材料,處理時應按《直接接觸藥品的包裝材料和容器管理辦法》第六十五條規定處理,即“對使用不合格藥包材的,藥品監管部門應當責令停止使用,并處1萬元以上3萬元以下的罰款,已包裝藥品的藥包材應當立即收回并由藥品監管部門監督處理”。
第三種意見認為,不能將該批藥品定性為劣藥。雖然國家明令淘汰使用安瓿包裝粉針劑,但是安瓿作為藥品包裝材料并沒有被淘汰,而是廣泛地被應用到水針劑等其他藥品上,D批號注射用輔酶A所用的藥包材安瓿是具有藥包材注冊證的合法藥品包裝材料,所以不符合《藥品管理法》第四十九條第三款第(四)項“直接接觸藥品的包裝材料和容器未經批準的”規定,不宜定性為劣藥。
評析:
筆者認為,在分析本案之前,有必要對安瓿和西林瓶以及它們對藥品質量的影響做一簡述。2002年,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在《淘汰落后生產能力、工藝和產品的目錄》(第三批)中將安瓿包裝粉針劑作為落后生產工藝予以淘汰,取而代之的粉針劑藥品包裝材料為西林瓶。西林瓶又稱鈉鈣玻璃模制注射劑瓶,是一種膠塞封口的小瓶子,有棕色、透明等種類,一般為中性玻璃材質;安瓿是瓶頸部較細的密封玻璃瓶,一般用做碘酒瓶、注射液瓶、口服液瓶等,在價格上西林瓶高于安瓿。
國家之所以淘汰安瓿,是因為我國企業目前使用的安瓿材質普遍是低硼硅玻璃,其質量較差,玻璃屑較多,且易存在脫片現象,不符合國際中性玻璃要求。直接接觸藥品的包裝材料和容器是藥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伴隨藥品生產、流通及使用的全過程,它們的質量直接決定著其是否污染容器內的藥品,以及是否影響該藥品的穩定性。由于藥品包裝材料、容器組成配方、所選擇原輔料及生產工藝不同,有的組分可能被所接觸的藥品溶出,或與藥品互相作用,或被藥品長期浸泡腐蝕脫片而直接影響藥品質量。安瓿就是這種經常發生組分被所接觸的藥品溶出、極易出現玻璃脫片現象的包裝材料和容器,但由于這種現象在常規藥檢時很難被發現,因而細微的玻璃脫片便有可能堵塞患者血管形成血栓或肺肉芽腫,進而影響患者的生命安全。所以,直接接觸藥品的包裝材料和容器對藥品的質量安全至關重要,安瓿被淘汰也理所當然。
本案中,C生產企業使用淘汰的價格便宜的安瓿來包裝粉針劑,這從某個側面反應映了該企業對藥品包裝、包材與藥品質量關系認識不清。為降低生產成本而使用淘汰的包裝材料包裝注射用輔酶A,這一行為給公眾用藥安全帶來了嚴重隱患,增加了藥品使用過程中的不安全因素,因此必須予以嚴厲打擊。但本案的特殊之處在于,安瓿雖然在粉針劑包裝行列被淘汰,但作為藥品包裝材料,它還沒有被淘汰。從案情中可知,D批號的注射用輔酶A所用的包材安瓿是具有藥包材注冊證的合法藥品包裝材料,這種情形下,該安瓿是否依然符合《藥品管理法》第四十九條第三款第(四)項“直接接觸藥品的包裝材料和容器未經批準的”規定呢?
是否符合《藥品管理法》第四十九條第三款第(四)項規定的情形,取決于如何理解“直接接觸藥品的包裝材料和容器未經批準的”含義。該條款本身并不復雜,但理解的關鍵在于“批準”二字。對于“批準”的理解,執法人員容易和《藥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條第三款第(二)項中“依照本法必須批準而未經批準生產、進口……”的“批準”意思等同,即指產品本身的審批并取得批準文號。如果這種理解成立,那么本案中的情形顯然不符合該條規定,因為該安瓿是取得了藥品包裝材料注冊證的合法包材,似乎第一種意見是正確的。
《藥品管理法》第五十二條第一款規定:“直接接觸藥品的包裝材料和容器,必須符合藥用要求,符合保障人體健康、安全的標準,并由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在審批藥品時一并審批。”該條第二款規定“藥品生產企業不得使用未經批準的直接接觸藥品的包裝材料和容器”,該條款說明“審批”和“批準”之間是有一定關聯的。《〈藥品管理法〉釋義》對該條的解釋是:“按照本條規定,直接接觸藥品的包裝材料和容器由藥品監管部門在審批藥品時一并審批。藥品生產企業在依法報請藥品監管部門審批新藥或仿制藥生產時,應當將擬使用的直接接觸藥品的包裝材料和容器同時報經藥品監管部門審批,經批準后方可使用;未經批準的直接接觸藥品的包裝材料和容器,其質量指標是否符合藥品要求和標準,未依法得到確認。為確保藥品質量,保證人民用藥安全,本條明確規定,禁止藥品生產企業使用未經批準的直接接觸藥品的包裝材料和容器;違反這一規定,使用未經批準的直接接觸藥品的包裝材料和容器的藥品,依照本法第四十九條的規定,將按照劣藥論處。”由此可以看出該條中的“批準”應包含兩層含義:其一,直接接觸藥品的包裝材料和容器本身應該是經過審批、拿到批準文號的產品;其二,直接接觸藥品的包裝材料和容器應是藥品監管部門在審批藥品時一并審批的品種。基于此,本案中的安瓿雖然具有藥包材注冊證,但其并不符合上述第二層含義,因此可以將其定性為《藥品管理法》第四十九條第三款第(四)項規定的“未經批準的直接接觸藥品的包裝材料和容器”;而用該安瓿包裝的注射用輔酶A就應定性為劣藥。
綜上可知,第二種意見是正確的,第一種意見理解是片面的。第三種意見認為應按《直接接觸藥品的包裝材料和容器管理辦法》第六十五條以使用不合格包材處理,這種理解是不正確的。因為不合格藥包材的定性需要法定檢驗報告方可定性,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適用該條規定處理本案并不妥當。